鲁迅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污点?鲁迅贪吃 , 贪吃到和儿子
争!零!食!鲁迅还是一个超级零食控 。
家里 , 总是零食不断 , 写文章时常常零食不离口 , 一边写 , 一边吃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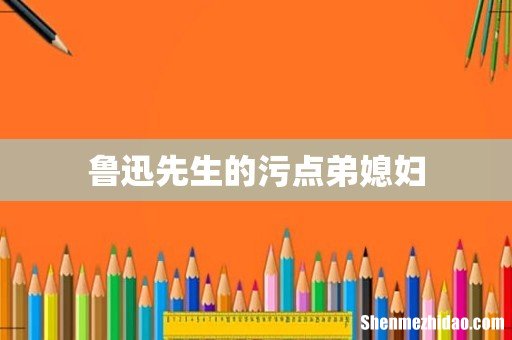
文章插图
在他的日记中光是提到糖果 , 就有饴糖、干焦糖、柠檬糖、柿霜糖、核桃糖、玫瑰酥糖、咖啡薄荷糖等多种品类 。尤其是柿霜糖 , 这是鲁迅最喜爱的甜食之一 。
柿霜糖是一种河南名产 , 圆圆的黄棕色的小薄片 , 吃起来又清凉又细腻 。
鲁迅第一次吃到这种糖 , 是一位友人特地带给他品尝的 , 他一尝觉得确实是好吃 。后来又听许广平说这是河南的名产 , 是用柿霜做成的 , 性凉 , 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 , 用这个糖一搽 , 便会好 。
鲁迅听了感叹道:“怪不得有这么细腻 , 原来是凭了造化的妙手 , 用柿皮来滤过的 。”可惜待到许广平向鲁迅说明柿霜糖的妙用时 , 鲁迅已经将刚得到手的柿霜糖吃掉了一大半 。
听完许广平的介绍 , 鲁迅连忙将所余的收起 , 准备在将来嘴角生疮的时候 , 好用这个糖来搽 。
但是到了夜间 , 鲁迅就忍不住了 , 将自己藏起来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 , 而且一边吃还一边安慰自己道:“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 , 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 。”不料一吃 , 就又吃掉了一大半 。
鲁迅留学日本时曾参加过光复会 。这是一个以组织暗杀和会党起义为主的反清组织 , 年轻的鲁迅以其激烈的救国热情成为这个组织的积极分子 。当时的光复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 , 结果被恩铭的亲兵剖腹挖心 , 消息传到东京 , 鲁迅在集会中义愤填膺慷慨陈辞 , 大有“引刀成一快 , 不负少年头”意思 。但是不久另一个刺杀任务被派到他的头上 , 鲁迅最初答应了 , 但临行之前却又退缩 , 理由是他有母亲需要奉养 。这个理由当然真实 , 鲁迅事母至孝 , 我们一直都知道 , 但是如果内中没有一点贪生怕死的因素 , 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人相信的 。
鲁迅兄弟媳妇是日本人吗 羽太信子:她是日本人 , 随周作人来到中国 , 并最终死在这里 , 于她来讲也算客死异国了 。许多写周作人的文章都会捎带零星地涉及一些她的行迹 , 其中有赞有弹 , 褒贬不一 。但有一点 , 大家似乎不约而同 , 即 , 她对周作人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影响非同小可 。周作人一生中至少有两件大事 , 羽太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。一是周作人与乃兄鲁迅的决裂 , 一是周作人“七七事变”后没有南下而留在北平 , 并最后落水出任伪职 。
关于前一件事 , 最有代表性 , 大概也最为可信的记述来自周建人 。周建人似乎对这个日本嫂嫂颇有微词 。他在《鲁迅与周作人》一文中有如下的记述:“增田涉说:‘他(指鲁迅)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(他自己那里没有小孩) , 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 。他用充满伤感的话说:好像穷人买东西也是脏的 , 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 。’鲁迅对我说的是 , 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:‘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 , 让他冷清煞 。’”在周建人看来 , 鲁迅与周作人夫妇的隔阂主要源于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 。羽太信子惯于挥霍 , 可以说“挥金如土” 。“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 , 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 , 有时还到处借贷 , 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 。”而鲁迅则自奉甚俭 。自己挣钱别人花 , 花钱的人又不心疼 , 过于大手大脚 , 且理直气壮 , 鲁迅看不过 , 气不顺 , 也是可以理解的 。他劝过周作人 , 但周作人作不了夫人的主 , 大哥的规劝只当耳边风 。后来 , 羽太还把她的许多亲属接来一起住 , 一切吃穿用度完全日本化 , 花销就更大 。终于导致鲁迅先是分炊 , 后彻底搬出八道湾 。鲁迅在1926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那天下午他去八道湾取东西 , 与弟弟和弟媳发生的一场冲突 。中有“其妻向之述我罪状 , 多秽语”等语 。至于究竟是什么“秽语” , 外人不得而知 , 虽后人多有揣测者 , 但到底只是揣测而已 。根据鲁迅这个记载判断 , 这个羽太信子的性格可能是相当泼悍的 。对这一性格特点 , 周建人还举了一个例子 , 他说:“早在辛亥革命前后 , 他(周作人)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 , 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 , 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 , 周作人发愣 , 而他的郞舅、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 , 从此 , 他不敢再有丝毫‘得罪’ 。相反 , 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 , 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 。”周建人说周作人是意志薄弱、性情和顺 , 却不辨是非 。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是“昏” 。这兄弟俩的意见倒也一致 。看周作人的文章 , 觉得他是那么渊博、见识又是那么卓超 , 但在世事上、大节上的处理与选择却又如此“出人意表” 。用乾隆皇帝对纪晓岚的评价“读书多而不明理”来评价周作人大体不错 。这一事件中 , 羽太信子起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 。
至于“七七事变”后 , 周作人没有南下而留在北平并最终落水出任伪职一事的原因 , 周作人自己及相关人等 , 都给出了不同说法 , 这一点人们都耳熟能详了 , 不用细表 。但个中真相却谁也说不清 , 至今也没有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 。不过官方的评价似乎还是汉奸 , 这一顶帽子想拿下来也难 。1937年后周作人留在北平 , 这件事中羽太信子扮演了什么角色 , 也没有见过专门讨论此事的文章 。估计一是不好写 , 一是当事者多三缄其口 , 一是这事本身并不重要 , 所以人们也就不去关注了 。如果考虑到羽太信子在促成他们兄弟反目中的重要作用 , 也就可以想象得出她对周作人当年决定去留的影响了 。其实 , 从鲁迅和鲁迅母亲及朱安搬出八道湾以后 , 八道湾的实际主人就已经是羽太了 , 鲁迅其时就说过 , 八道湾就剩下一个中国人了 。虽然鲁迅搬走以后 , 周建人又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, 但不久也去了上海 。这样 , 周作人实际上已经处于日本人(羽太信子和她的娘家人)的包围之中 。加上羽太信子泼悍的性格 , 周作人无论生活上、还是精神上恐怕都要受制于她吧 。许多人喜欢从更深层的原因分析周作人的留平与落水 , 倒更愿意相信羽太信子的直接而巨大的作用 。
羽太信子不仅对自己丈夫的人生道路有着负面的影响 , 她对自己的妹妹芳子(也就是周建人的妻子)的成长也没有起到好作用 。俞芳引述鲁迅母亲的话说 , 芳子长年和信子在一起 , 受信子影响很大 , 比如 , 贪图享受 , 爱虚荣 , 怕过艰苦的生活 , 对周建人不够体贴 , 不太近人情等等 。
以上说的羽太信子基本上是一个灰色的 , 甚至是不光彩的形象 。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记述了她的生活的另一面 。鲁迅母亲说信子勤劳好学 , 有上进心 。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也不能说不上心 , 比如 , 鲁迅母亲有肾炎 , 需要吃西瓜 , 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 , 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 。这让老人家很满意 。信子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周到得很 。另外 , 徐淦《忘年交琐记》长文中专有一节记羽太信子 。徐文说:“上街采办 , 下厨做饭 , 扫地抹桌 , 洗洗刷刷 , 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 。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 , 鞠躬如也 , 低声碎步 , 温良恭俭让 , 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 , 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 , 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 , 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。”文洁若先生在《晚年的周作人》文章中 , 记了羽太信子的两个小细节 , 很能说明一点什么 。其一 , “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 , 每餐必先在牌位(周氏兄弟母亲鲁老太太、周作人女儿若子、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)前供上饭食 , 然后全家人才用膳 。”其二 , “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 , 讲的居然是绍兴话 , 而不是日语 , 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 。”这第二个细节是文先生听来的 , 她自己并未亲见 。而据徐淦记述 , 羽太信子是“说不上几句像样的绍兴话”的 。如果文先生记载的这第二个细节可信的话 , 倒真是让人感慨的 。
总的来讲 , 羽太信子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女人 , 她因为嫁了一个有大才、有大名的丈夫而为世人所知 。她又因为身处一个夫妻各自所属民族国家之间激烈争战的时代 , 而身不由己地多多少少地卷入了 。这种民族国家之间不正常关系对个体的影响体现在她身上 , 就是她的丈夫在民族大节上的首鼠两端、进退失据 , 终于堕入魔道 , 也使她在战争之后的生活受到连累 。设若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 , 她也许能够平平静静地、更感幸福地走过一生吧 。不过 , 几十年后的今天 , 我们要是要求她在当年那样的历史关口 , 敦促自己的丈夫离开北平南下救亡也是不现实的 , 也是苛求她了 。更何况她的见识、她的民族属性也使她不能这么做呢 。望采纳 。
鲁迅 兄弟媳妇羽太信子 , 原本伺候周氏兄弟的酒家女儿 , 不知道怎么和周作人好上 , 从后来她善于待客给人的印象 , 好起来也有那种日本妇女卑下可人的风味 , 真把男子伺候的主子一般舒服 。
从她的癔病和暴烈的脾气 , 似乎周作人不该喜欢她 , 但这是起初不知道的 。相反 , 他大大咧咧花钱享受的脾气 , 倒正合了周作人百事任性而不经心的脾气 。
吊轨的是 , 她的闹病反倒成了拿住周作人的手段 , 周作人起初为了她不闹 , 随便满足她 , 及至懂得了这是一种病 , 他小兄弟说 , 已经养成奴隶性 。很可能到了中国 , 羽太信子才满口支那长日本短 , 把民族身份当成骄傲 , 寻求保护和要挟夫家的资本 , 周作人受她一辈子嘴巴里不干不净的辱骂自己民族 。她一辈子不说中国话的 , 只有死前梦里说几句绍兴话 。周作人解放后有一回在兄弟面前失态 , 说自己做的一切(当汉奸)都是为他们(家庭) 。
她还嫌自己孤单一人不满足 , 把妹妹芳子弄来中国 , 居然一辈子做她下女 , 呼来喝去 。姐妹同谋 , 把周建人骗婚 , 也制造了一出日后的悲剧 。
鲁迅等人一直说 , 和信子的矛盾是经济上的 , 她任意花全家的钱 , 而毫不听劝(连养给埃罗先科的鸭子 , 都吃比大鱼大肉还贵的日本进口鸭食) , 鲁迅有些刺儿头 , 她就始而冷落 , 后来分灶(但周作人只顾忙自己的 , 还没有来得及知道 , 很可能看见不对劲时才起疑 , 这比较要命) 。兄弟失和前一天 , 巧了信子刚好发病(她如何会发病 , 是否给周作人下药 , 故意归罪大哥?) 。
【鲁迅先生的污点弟媳妇】她后来坚持把父母接来中国 , 却不孝的可以 , 以至于日本老人泪眼滂沱的找鲁迅的母亲和朱安诉苦 , 后来终究送回去 。看了两地书中惹人笑的这么一个段子 , 叫人生出什么感想 。
陈西滢和鲁迅的关系?1、陈西滢和鲁迅的关系:
因为女师大风潮 , 激起了鲁迅先生与陈西滢先生之间的笔战 , 所以两人的关系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 。
2、形成这种关系的具体原因:
在20年代中期 , 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与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、"闲话"作家陈西滢之间发生过一场论战 。这场论战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为发端 , 引出了一系列的笔战 , 也同时涉及到了对对方作品的评价问题 。1927年 , 陈西滢发表《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》一文 , 是他向读者推荐的新文学杰作 。他对鲁迅小说及杂文的评价颇有意味 。
陈西滢所列十部著作包括:胡适的《胡适文存》 , 吴稚晖的《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》、顾颉刚的《古史辨》、郁达夫的小说《沉沦》、鲁迅的小说集《呐喊》、郭沫若的诗集《女神》 , 徐志摩的《志摩的诗》、西林的戏剧《一只马蜂》、杨振声的长篇小说《玉君》以及冰心的小说集《超人》 。应当说 , 陈西滢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总体较为冷静客观 , 并无拔高之嫌 , 但态度也不均衡 。尤其对鲁迅小说的评价 , 与后人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出入较大 。
陈西滢认为《孔乙己》、《风波》、《故乡》是鲁迅"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们风物 , 都是好作品 。"但又说 , 小说里的"乡下人" , "虽然口吻举止 , 惟妙惟肖 , 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 , 皮毛的描写 。"即使只肯定了这些小说的描写风土人情的好处 , 也不忘大打折扣 。他同时更不忘表示对鲁迅杂文的不恭 。在文后的说明中 , 陈西滢说了一段别有意味的话:"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 , 就不说他的小说好 , 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 , 就称赞他其馀的文章 。我觉得他的杂感 , 除了《热风》中二三篇外 , 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 。"
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 , 至少说明 , 一个批评家要真正做到"好处说好 , 坏处说坏"谈何容易 , 作品之外的观点、立场 , 常常会成为左右批评标准的障碍 。
